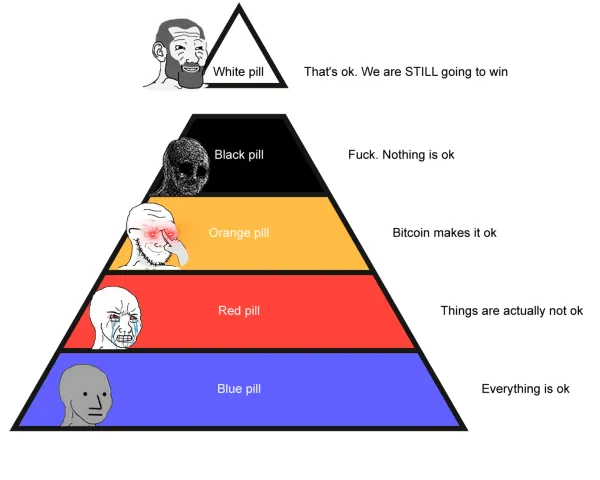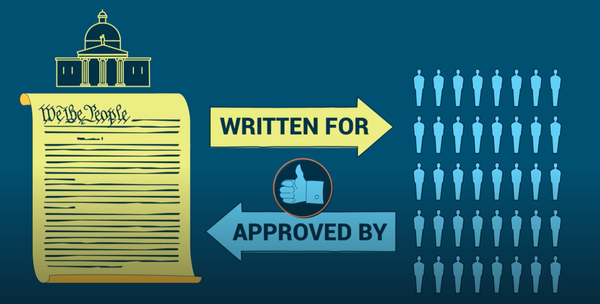仇恨言论也是言论自由
最高法院认为,俄亥俄州的法律没有区分两种情况:一种是提出可能涉及暴力的观点,另一种是煽动迫在眉睫的违法行为。根据第一修正案,前一种言论在宪法上是允许的,而后一种则不受保护——因为它会直接引发暴力,即“迫在眉睫的违法行为”。换句话说,只有当言论带来切实、具体、立即的危害时,才可以受到限制。

言论自由与布兰登堡案
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。事实上,它正是民主的核心。
它能够促进理性的讨论,让公职人员承担责任,并营造一个思想市场,不同观点在其中交锋、碰撞、检验——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。
如果公民不能畅所欲言,他们也就失去了自由。
正如十九世纪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·道格拉斯 (Frederick Douglass) 所说:“在开国元勋们看来,没有哪一项权利比言论更神圣。在他们眼中,它是社会和政府的伟大道德革新力量。”
《宪法》第一修正案明确写道:“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……剥夺言论自由……”
但是,言论应该自由到什么程度?
显然,言论也必须有限制。
在1919年的申克诉美利坚合众国 (Schenck v. United States) 一案中,大法官奥利弗·温德尔·霍姆斯 (Oliver Wendell Holmes) 著名地指出:你不能在拥挤的剧院里虚假喊“着火了”,因为那可能引发恐慌,导致伤亡。那么,煽动他人实施暴力的言论呢?还有如今所谓的“仇恨言论”,它是否应当受到保护?
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。最高法院为此争论了几十年。
布兰登堡案的背景
1969年的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 (Brandenburg v. Ohio) 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
没有多少裁决能像它一样,深刻界定了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与不受保护言论的边界。
克拉伦斯·布兰登堡 (Clarence Brandenburg) 是三K党 (Ku Klux Klan) 俄亥俄州分部的头目。三K党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,激烈反对民权运动。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战争结束时,长期以来代表着种族主义与恐怖,其白色头罩和燃烧的十字架已成为恶名昭著的象征。
1964年夏天,布兰登堡邀请辛辛那提的一位记者拍摄三K党的集会。电视画面中出现了戴着头罩、手持枪械的三K党人,他们正在焚烧十字架。
在一份充满种族侮辱的声明中,布兰登堡说:“我们不是复仇组织,但如果总统、国会、最高法院继续压制白人高加索人种,可能不得不采取报复。”
布兰登堡显然没什么学问,他原话中使用的“revengent”和“revengeance”这两个词根本不是英语单词,但他的意思却一目了然。
他还宣布,三K党将在整个南方举行游行,计划从7月4日美国独立日开始。
正是因为这些言论,布兰登堡依据俄亥俄州法律被定罪。该法律规定,任何人与他人“共同倡导”犯罪、暴力、破坏或恐怖手段,作为实现政治改革的“必要或正当方式”,都属违法。
二十世纪初,美国各州相继通过了类似法律,以确保公共安全,抵御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威胁。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,这类威胁似乎尤为逼近。
然而,这些法律含糊宽泛,缺乏明确界线。它们没能清楚地区分哪些言论应受保护,哪些言论应受惩罚。比如在俄亥俄州法律中,“倡导”暴力政治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?
最高法院的判决
布兰登堡提出上诉。1969年6月9日,最高法院裁定对他有利。法院援引了《诺托诉美国案》(Noto v. United States, 1961) 的先例,该案指出:“只是抽象地宣讲……并不等于真正组织一群人准备采取暴力行动。”
最高法院认为,俄亥俄州的法律没有区分两种情况:一种是提出可能涉及暴力的观点,另一种是煽动迫在眉睫的违法行为。
根据第一修正案,前一种言论在宪法上是允许的,而后一种则不受保护——因为它会直接引发暴力,即“迫在眉睫的违法行为”。
换句话说,只有当言论带来切实、具体、立即的危害时,才可以受到限制。布兰登堡在讲话中使用的是假设语气——“可能不得不采取报复”——因此他的言论不符合法院确立的“迫在眉睫的违法行为”标准。
虽然布兰登堡的仇恨言论理应受到谴责,但法院认为,审查这种言论反而对自由社会的威胁更大。
自由社会的标志
为了维持权力而压制异议,这是威权政权的典型特征。
第一修正案保障政府必须保持内容中立。它不能偏袒或打压某一种思想、观点或声音。一个真正的自由社会,必须容忍令人反感的言论,甚至是所谓的“仇恨言论”。唯一的例外是那些直接导致暴力的言论。
言论自由必然伴随着代价。人们可能因此而受到冒犯,甚至深受伤害。但在布兰登堡案中,最高法院认定,这些代价被言论自由带来的益处所抵消。
应对仇恨言论的最好方式,是让更多的声音加入公共讨论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守护这一最不可或缺的自由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www.prageru.com/videos/brandenburg-v-ohio-hate-speech-is-free-speech